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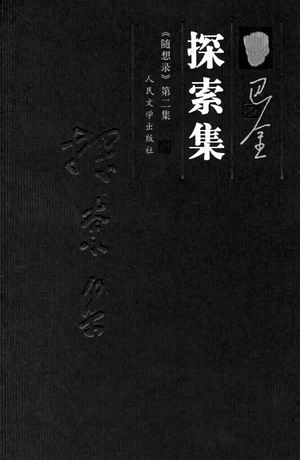 |
巴金:《病中集》、《探索集》(香港三联)
认识巴金先生是很遥远的事了。
那时我们正发着作家梦,班上的同学看到北大同学出了本《红楼》文艺杂志,我们没钱出纸本,就出墙报式的《雨后笋》。请徐震锷老师写了刊名,会画画的同学王维宜负责装饰、插图,同学稿经同学选出的编辑处理后,全贴在一个大黑板上,诗、散文诗、寓言、散文、短小说、文学短论,还算多样。一切做妥帖了,就摆在文史楼前,出版了。反应奇好,一本挂在黑板上的小本子,读者写了不少鼓励的话,丽娃河西的外语系和理科同学,还要求摆到河西去。编辑中有沙叶新,我,大概七八人,有两个已下世了。
就在那年,沙叶新在《萌芽》上一下子发表了两篇小说《老鹰篮球队》、《美国剧院的悲剧》,我的一篇已三校,清样也寄来给我校看过了,且决定下期发表。最后到老总那级给撤下了,理由是杂志出口,怕给人“输出革命”的口实。我写的是马来亚抗日军后代的故事。到第二年才在《少年文艺》登了篇小说。之前,有次中文系秘书把我叫去,秘书告诉我:“你投给新民晚报的稿,报社决定要用,要系里出示作者的政治面貌证明。我已去信了,说你没问题。等着收稿费吧。”秘书好像也很高兴,总是笑着跟我说话。我才知道稿要发表还有政审作者这回事。
大概是1958年,沙叶新和我成了《萌芽》的“培养对象”,有活动就寄信来叫我们参加。
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,上海作协办了个“作家见面会”,我俩都给邀去了。现在留下印象的作家,只有巴金、魏金枝、胡万春。他们每人坐在一张桌子前,桌上还放了座台灯,像一个个看相的摊位。我们一见到巴金就拥了过去,问好之外,还说些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留下了。留下的只是当年的兴奋,和拥来拥去的人群的情景。
“文革”期间巴老被批斗,始知他有30多万存款,是一个不拿政府工资的真正作家。
1984年10月,巴金先生来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。那几天香港报纸热闹了一阵。马国亮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,时已移居香港,任《良友》画报顾问,他和巴老约定23日下午去中大宾馆拜访他,《良友》准备做报道。我当时是执行主编,带了摄影记者同去。中大宾馆宽大敞亮的厅里,随巴老访港的李小林、陈丹晨亦在座。那时大陆气候还是乍晴乍寒时节,我问了些较尖锐的问题,后来听说陈丹晨颇有微言。这次探访,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了不少照片。现在回看照片,还真有一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戆气,失礼得很。
巴金先生为每人题赠两册香港三联刚出版的《病中集》、《探索集》给我们。用圆珠笔题上:赠××先生/巴金/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三日。字写得很轻,颇小。若不是巴老写下的日期,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的事了。
年轻时看过他不少小说,有的小说还带点洋味。最喜欢的不是他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而是他的《春天里的秋天》,可能与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厦门鼓浪屿有关吧。
董桥:《这一代的事》(圆神)、《从前》、《小风景》、《白描》、《记忆的脚注》、《甲申年纪事》、《故事》(牛津);台湾远流版《天气是文字的颜色》等六册。
 《明报月刊》在我来港不久就爱读,曾到旧书摊搜集了不少往日的旧刊。胡菊人与董桥任主编时,几乎期期都买来读。后来因搬家全丢弃去,现在仍觉可惜。
《明报月刊》在我来港不久就爱读,曾到旧书摊搜集了不少往日的旧刊。胡菊人与董桥任主编时,几乎期期都买来读。后来因搬家全丢弃去,现在仍觉可惜。
认识董桥是任明报出版社经理的哈公介绍的。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稿,他可介绍给《明月》,正好我有篇写金石家吴颐人的稿,径去写字楼找他,他即介绍我给董桥,那篇稿也刊发了。初见董桥,觉得他有些内向还带点羞涩。大概是1985年,我们相约在铜锣湾的印度尼西亚餐厅午饭。谈到他的文章,我说他用词造句受明小品的熏染,他说:他更多是受英国小品的影响。还说:掌握好一门外语,回头再读中国典籍,就有新的感受。但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句话:“每篇文章都改了六七遍。”
这是我认识他外冷内热的一面。
他送我的第一本书是《这一代的事》。《双城笔记》是他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,早已绝版。1995年,书店“小说精品店”(今改名铜锣湾书店)开业,一日与陶然、梅子闲逛,上得楼去,见一叠《双城笔记》,买得回来,禁不住写下“偶遇于小说精品店,爱而购之”,寄给董桥要他题几个字。寄回时,他题了“少作教人脸红,深悔当年眼低手低;古剑兄竟将之出土,不敢不认,聊题数语,以志污点。”自谦而幽默。加上牛津版的《伦敦的夏天等你来》、《保住那一发青山》、《没有童谣的年代》、《回家的感觉真好》,惟缺一本1982年素叶版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与胡须丛外》。今年在老友叶辉书架上得见,欲讨来占为己有,他亦慷慨赠与,不亦快哉,快何如之。
董桥的随笔我喜其精致,用词运句之精巧雅驯,比喻之尖新,取题典雅别致。用散墨、眉批古语词汇为辑名,有惊艳之喜,带出新鲜感,渗出一缕缕书香。最为惊动文林的是他以武侠小说笔法,写中英谈判的“编者话”,独创一格,义隐而情深,引来一片好评。
校友王璞初来香港,曾向我打听香港哪些人的文章好,我首个推荐的就是董桥。我说:他的文章很“文”。这已很足够说明他的特色了,文采,文人气质,文质佳妙。
董桥走入大陆读书界,罗孚于《读书》上发的《你一定要读董桥》一文,居功至伟,随后是陈子善。大陆出版董桥作品集,少说也有六七本,读者甚众。若其文字不好,上帝推荐也难见其效的。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故事》,初版二万册,未逾90日,已再版上市。再上一本《旧时月色》(选本),据编者胡洪侠告知,已印六七万本。羡慕是羡慕不来的。
他的书可谓享誉两岸三地。两岸以其为硕士、博士论文的,也不少见。
 董桥赠书给我,都题上数语,尤可玩赏,录一二供同好欣赏:
董桥赠书给我,都题上数语,尤可玩赏,录一二供同好欣赏:
《小风景》题:“放翁诗云:人间万事消磨尽,唯有清香似旧时。此书文字风华消磨尽,只有那几十幅丹青堪供古剑老兄消闲。”
《白描》题:“文似看山不喜平,友如作画须求淡。上句说《白描》不足为贵,平平无山也;下句说文人要不相轻,交情应如淡墨,不漫不漶,千秋常新。古剑以为然否?”
不录了,文人意趣尽在其中,多则无味,正如粤语所云:少食多滋味。
林海音:《剪影话文坛》、《家住大书坊》
林海音送过我不少书,一是送走了,一是我自作孽,毁了。因替香江出版公司编一册《林海音散文》,当时太忙,更没时间去影印,就把她的三本书肢解了,取出所需,余骸就丢去了。她的一些小说和其它台湾书后来都送给了《台港文学选刊》。
林海音是我接触过最让人感到亲和的作家,热情细心对待每个人,对着她你只会感到亲切与和善。
和她认识有点偶然。一天在中大任教的画家刘国松约我上他家吃饭,他家来了位居美的超写实派画家夏阳。回程时刘要我带夏到铜锣湾的柏宁酒店,见他的婶母林海音和夏承楹――他们来港开中文报业年会。到了酒店,她见我是《良友》的,即问:“是以前上海的《良友》吗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得到肯定的答复,她更来劲了,拉我过去见她先生,指着他对我说:“他们兄弟俩的花样滑冰照片上过《良友》,一大版。”最后她又提出:“你能复制一套胶片给我们吗?”我说:“可以,马国亮先生一定有办法。”
以后她收到胶片,一再表示太高兴了,还收入他们的书中。是的,这牵回多少前尘往事,那些在北京的青春岁月啊。
我最早读到她的文字,是台湾联合报上她的专栏连载“剪影话文坛”。每晚发完稿等看大样的间隙,就看她的专栏,对她交游广阔和台湾文坛有所了解,对她已不陌生。
友谊就这样开始。我首次去台,她约了一些作家和我吃饭。事前,先来电话把名单念了一遍,又问了一句:“有不适合的吗?”没有――她担心有些人我不喜欢,坏了气氛,然后再问了一句:“你还要请什么人吗?”她就是这样细心,所以她请客的场合,都是皆大欢喜。她在台湾文坛广受尊重,人人称她林先生,她的家就是台湾半个文坛。这次她送了不少书(还有其他朋友),上飞机行李超重,还补了钱,但收获了友谊。
在《良友》出她的专辑时,我写了篇《杂写林海音》,自己觉得写得不好,自己撤下;约另一个人写,看了稿也不觉得好,只好上。后来我那篇文章收入《梦系人间》一书,寄给她。她看后说,很好啊,你为什么不用呢。
林海音年轻时是个美女,年纪大了,变得富态了,仍称得上美。女人都爱美,林也不例外。也是那一次去台北,她请了几位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、应凤凰数人和我去广东酒楼饮茶(林曾出钱给上述数人出版《文学史料》杂志),我要给她拍照。她笑着说:“不要拍正面,不好看,稍微侧点好看。”她就这样率真。
回港后,还来通道歉,说因太忙,只见了我两次。
说她率真,还有件事可记。我要给他编散文集的事传出去,有家出版社找上她,也要给她出书。她不客气地回绝,要我对那人说:“我不知你是谁,我的书不是随便给人出的。”把人家打发走了。北京某机构出版系列台湾文学作品,请林做顾问。她回信说,我不做光头顾问,既做就又要顾又要问。她是这样的人。
她来香港指定要看大陆电影,我联络到发行大陆电影的南方公司,在试影室满足了她的好奇。第二年来港,她就倒霉了,住在九龙的青年会旅舍,被小偷光顾,不见四千多美元,报了警也没结果。但看大陆电影的热情未减,还带来另一女书法家董阳孜和画家陈其宽。林与陈都喜欢拍照,还教我随身带个相机,把有意思的东西拍下,留作纪录。可惜我未听教,很多场景就从脑中消失。有张在南方公司看电影的照片,还是陈画家寄来的,不然也记不起当时是些什么人了。
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,是与九歌、洪范、大地等齐名的出版社。她的主要助手夏祖丽移民澳洲,她也年纪大了。结束出版社时,她把版权还给作者,把余下的书送给作者,愉快地谢幕。她这一生是快乐的。
台静农:《大千居士临瘗鹤铭》
《瘗鹤铭》是镇江焦山栈道岩上的摩岩石刻,后因山石崩塌落入河中,至北宋才发现,但已残缺,不知何人书。其书法备受推崇。黄庭坚评为“势若飞动”、“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”,明代王世贞曰:“古拙奇峭,雄伟正逸,固书家之雄。”
2006年与同学游扬州、镇江。一日游焦山碑林,见墙上贴着数方不规则的石刻,是《瘗鹤铭》塌落河中的原刻,举起相机拍了数张,从荧屏上看并不清晰,很感遗憾。后在小卖部看到一册鹤州本/水前本的《瘗鹤铭》,购回作纪念,亦想回来后与张大千临本对照。
台静农与张大千交厚,大千居土将第六次临本送给台先生。台先生将其印行。
1987年我二度赴台,出版家何恭上领我去拜访他。那时他还住在温州街的日式房子里,天井有大水缸养着莲花。跨过天井,就是朴素的客厅,一张大桌,左角乱叠了书刊和笔筒里大大小小的毛笔。进去时他正在看香港的《大成》杂志,我还瞥见放在书籍上一幅饶宗颐的画。
我递上名片和上海书画家吴颐人的一幅汉简书法,就闲谈起来。谈些什么已不复记忆。
临辞去前,他取出一册《大千居士临瘗鹤铭》,在内页用毛笔题上“古剑先生存赏/台静农敬赠/丁卯初夏”。
这是我所藏台先生的书和字,很为珍惜。
这次倒记住了拍照,一张他叼着香烟题字,一张他手托下巴听说话,神情自然。当然还得感谢出版家朋友,为我和台先生拍了两张合影:一在室内,一在大门前。
他逝世后在报道中知悉,台先生一直珍藏着陈独秀的手迹,所幸那里没有抄家,此文物才得以保存。他那份对友人的牵挂也是感人的。
回家后,拿出大千居士临本与鹤州本/水前本《瘗鹤铭》对照着读。张大千不愧是大家,临得神采奕奕。
